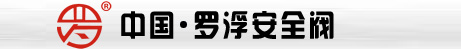
一、完善外资国家安审机制的必要性
维护国家安全是本次《外资法》立法目的之一。过去我国也有类似的国家安全审查规章,但法层级不高。为确保国家安全,规范外国投资,中国将建立统一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任何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进行审查。具体由国务院下设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负责。
外国投资者向中国外国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准入许可申请时应提交的材料中包括对是否触发国家安全审查的说明。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是我国外国投资主管部门审查外国投资进入中国的首要因素,一旦发现外国投资事项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将暂停准入审查程序,并书面告知申请人提交国家安审申请。《外资法》不仅规定外资并购中国国内企业时需进行安全审查评估,而且规定外资准入阶段也要进行安全审查评估。同时,还对违反者规定了惩罚措施。
一国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等目的对外国不良投资进行限制,防止外国资本对本国国家安全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已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在外资准入制度中,国家安全审查能阻断外资通过东道国各种投资便利化及优惠政策达到寻租目的,起到为国民经济“保驾护航”的“安全阀”作用。因此,要善于使用国家安全审查机制。
二、使用外资国家安审机制的谨慎性
《外资法》设计了外资主动申报、中国政府审查机构自主发起和利益相关者提请发起的三重外资国家安审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该机制的作用。
首先,正如“钱币有其两面”,善于使用不等于可擅自滥用。作为限制外资的手段,国家安审机制不应被滥用为阻止外资进入、排除竞争的“常规武器”。以为例,以国家安全审查为由否决外资并购的现象并非如传言般多。如下表统计。
其次,由于行政机关在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时所考虑因素的相对主观性,以及国家安全概念内涵模糊性与外延扩大性趋势的存在,导致国家安全审查与“开放投资”始终存在一个比例性的平衡问题,这值得注意。
再次,《外资法》较具体地规定了外国投资者向国务院外国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国家安全审查申请时应提交的材料。当然,具体要交哪些材料,在实践中仍有待明确。特别是《外资法》中规定的“等”材料(信息)的外延是什么?这些都会引出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问题。“预约商谈”、提供《安审指南》或许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最后,《外资法》中规定的安审因素有十大类,外加一个“兜底条款”。对这些因素的考量和概念的理解,也可能在实践中引起争议。为此,《外资法》专门设计了防范措施:“对国家安全审查决定不得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实际上借鉴了美国等国的做法。那么,这种排除规定是否意味着双边投资协定中用尽了“当地行政或司法救济”,从而可提交国际仲裁机构仲裁?或者说这种“自排除”规定就可排除将来国际投资仲裁机构的管辖?这些都还需要我们小心求证。《外资法》同时设计了一般的外资纠纷解决机制,即“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投资和经营活动中产生纠纷的,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协商、调解、投诉、复议、仲裁或者诉讼等方式解决。”这两者的互应性亦需关注。